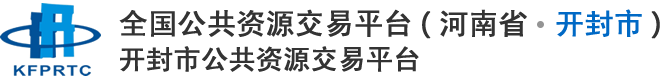刑鼎的奇怪与不奇怪
发布时间: 2024-12-06 16:26:12
浏览量:
发稿人:澳门传真正版
张剑锋
公元前513年的一天,在晋国国都绛城的广场上,一队士兵汗流浃背地运来了一座480斤重铸满了文字的大铁鼎。鼎是官方铸的,主持人晋国大夫赵鞅和荀寅都是晋国执政六卿中的骨干人物,不奇怪。鼎的内容也是官方的文件,是晋国前任正卿范宣子士匄于公元前550年制定的刑书,也不奇怪。然而,奇怪的是,这件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却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已近不惑之年的至圣先师孔丘先生,听到这件事之后捶胸顿足地大呼“完了,完了,规矩乱了,晋国要亡了!”(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孔夫子为什么要这样惊诧呢?拿他老人家的话来说就是,“贵贱不错乱,这就是所谓的规矩……现在废掉这个规矩,而铸造刑鼎,让老百姓从鼎上就能看到法律条文了,他们哪还能再尊敬那些贵族?贵族又怎能保守祖宗基业呢?贵贱等级没有了,还怎么治理国家呢?”(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如同夫子的其他著述一样,这段话也有些让人似懂非懂。为什么老百姓能看到法律条文就不会再尊敬那些贵族了呢?在此23年前另外一位老先生,晋国大臣叔向的类似评论就把孔子没有说透的这段话给说出来了。
当时郑国执政子产干了一件跟赵鞅和荀寅差不多的事情,也铸了一座大鼎,将国家法律条文铸在上边,并把鼎放在城中繁华之处向世人公布。此时的叔向老先生就像后来的孔子一样,表示惊诧莫名,他给子产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若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激幸以成之,弗可为矣”。这段话的意思就明白多了——为什么不要把法律明白写出来呢?就是要让老百姓没法跟贵族老爷们讲理啊!如果法律写出来了,老百姓就可以引用法律“以征于书”去对抗贵族老爷们啦!
的确,孔子和叔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要知道,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不是执法的人——因为他们只能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办事;甚至也不是立法的人——他们虽然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制定“游戏规则”,但一旦规则制定出来,他们仍然不得不受规则所约束;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是那些不想把法律条文写出来、他的话就是法律的人!按中国传统的说法,这叫做“口含天宪”。
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临事制刑,不预设法”,可以随意对平民及新兴地主用刑,权力可以说是大到了极点。即使有人制定了一些法律——譬如前面提到的晋国正卿范宣子所制定的《范宣子刑书》,也会被藏于秘府,为贵族所垄断,不能让百姓知道。只有保持这种神秘性和恐怖性,才便于贵族随意处置百姓。然而,刑鼎一铸,这种垄断被打破了,老百姓也可以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了,自然贵族阶级的权力也就被削弱了。
事实上,正如孔子和叔向所怀疑的那样,刑鼎的问世并不是某位卿大夫无意间的一时冲动,而是在奴隶社会日益衰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不断攫取政权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在刑鼎之中确实蕴含着削弱奴隶主贵族权力的意图。拿晋国来说,刑鼎的出现就有几个大的政治背景。首先是代表旧势力的晋君的式微。从晋平公开始(公元前557—公元前532年在位),晋国君权就开始逐步滑落,大权逐渐转移到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各家卿大夫手中,其中最有实力的就是韩、赵、魏、范、中行及智氏等六卿。前面提及的几个人物中,范宣子士匄是范氏族长,赵鞅(即赵简子,赵氏孤儿赵武之孙)是赵氏族长,荀寅是中行氏族长,都是六卿中的代表人物。范宣子制定刑书,赵鞅和荀寅再把它铸到鼎上,首先针对的就是晋君。有了成文的法律,卿大夫们就可以藉此与君权抗衡,而晋君则像被套上了紧箍咒,再也不能像70年前赵氏孤儿案中那样随意屠杀大臣满门了!其次是晋国六卿之间的竞争与平衡。六卿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竞争的一面,在晋国政坛上形成了各卿轮流坐庄,相互制衡的局面。在六卿中还没有哪家具备压倒性的优势,可以一举打破平衡、消灭其他对手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相对稳定的局面,获得和平发展的空间,六卿之间也需要通过协商建立一套共同承认的、能够用来调解彼此之间矛盾的游戏规则,而这正是刑鼎可以起到的作用。最后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六卿之下的士人(小地主阶级)、国人(城市平民)等群体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提升,六卿通过铸刑鼎的举动,也是在向这些群体让渡一部分权力,以取得笼络人心的作用。
果不出孔子所料,铸刑鼎的举动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导致了晋国的灭亡。随着晋君权力不断向卿大夫转移,在刑鼎铸就的 79年之后,公元前434年,六卿中剩下的韩、赵、魏瓜分了晋国的几乎全部土地,史称三家分晋。而晋君则从此开始名存实亡,并于58年后彻底从历史中消失。不仅晋国如此,以三家分晋为标志,中国由春秋迈进了战国,由奴隶社会走向了封建社会。
虽然这一切的后果对孔子这些旧制度的卫道士们来说是悲剧,但对其他人来说却未必。晋国和旧的奴隶制度是毁灭了,可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韩、赵、魏三国却代表了新生的、更为先进的阶级和生产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变法图强,他们将带领中国走向新的辉煌。不仅中国如此,全世界也都是如此。从广义上来看,铸刑鼎的举动实际上就是将法律明确化、制度化,不允许随意更改践踏。当然,不见得非要铸成鼎,甚至不一定要以法条法典的形式存在(明确的判例法制度也可以起到相同的效果)。这一做法的政治影响前面已经在晋国的例子里分析过了,而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可能更为深远的,则是前面尚未分析到的经济影响。要知道,对于经济,特别是对于工商业而言,要想实现健康发展,很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对未来的良好预期。在统治者“口含天宪”的时代,这样的社会环境和良好预期都是不会存在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游戏规则,统治者可以任意剥夺工商业者的财产甚至是生命。在一切都是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人们怎么能够期望工商业者们能够有长远的目光、积极地投资再生产呢?中国古代为什么工商业始终发展不起来?工商业者们一旦赚到一些利润,为什么不是拿去购置田产,就是肆意挥霍,很少有继续投资发展生产的?这与在中国铸刑鼎、健全法制的做法没能够继续推进下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因此,总体来说,刑鼎的铸造,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产物,是新生力量反抗旧势力专制统治的结果。赵鞅和荀寅铸刑鼎,是历史大势所趋,不奇怪。而孔子站在捍卫旧制度的立场上,看到了刑鼎对奴隶主专制的巨大威胁,从而跳出来骂刑鼎,从他的角度来看,也不奇怪。
然而,真正奇怪的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今天,却也有很多人、很多有关部门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阻碍着刑鼎的铸造。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阻挠的不是狭义上的铸一口鼎,或是以别的什么方式把某些法律条文记录下来。他们反对的是广义上的刑鼎,也就是说反对建立一套明确的、客观的、合理可行的法律法规体系,从而以此来保护自己的权力和这些权力所带来的利益。
这些人阻挠“刑鼎铸造”的方式方法有很多,其中比较直白的方法包括在法律法规体系中留下某些空白或是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或是搞一堆“内部掌握”的政策(与晋国把《范宣子刑书》藏于秘府何其相似)。但毕竟依法治国是当今国策,这种过于直白的方法不好用得太多。因此,更多的做法则是比较间接的。其一曰模糊:法规条文既可以这样理解,又可以那样理解,究竟怎样理解才对,只有有关部门说了才算,而有关部门每次说的也不一定一样,要一事一议。其二曰过时:多少年前的老皇历,早已无法适应当前的实际情况,也不废除或修改。遇到了事情,有关部门既可以照章办事,也可以与时俱进,全凭他一张嘴、一颗印把子。其三曰矛盾:政出多门,人人都要管,管法又各自不同,常常互相矛盾,不论你如何办事,总可以有部门跳出来说你做得不对,哪炷香没烧到都不行啊。其四曰无法操作:十天才能准备好的材料,硬是规定必须五天内交齐。既然你交不齐,违了规,那么有关部门就可以自由裁量了,最后是严格执法还是为企业、群众办实事,就全看你的“沟通工作”做得好不好了……办法有千般万种,目的却是一样,就是让老百姓没办法“不忌于上”,“以征于书”,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只能去求他有关部门大发慈悲。这就是权力!慈悲是可以发的,但显然不能随便发,需要做好“沟通”工作。这就是利益!
当然,上面指出的这些问题也有可能是无心之失,不一定都是蓄意所为。但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一天得不到解决,就一天铸不出真正的刑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就一天不能完全顺畅地推进。当然,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刑鼎铸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会有很多人站出来反对,他们未必像孔子和叔向那样坦白得可爱,而是可能找出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理由。而既得利益者们也就会顺水推舟地采纳他们的“合理化建议”。因此,要真正铸出刑鼎,我们就有必要引入对权力的制衡,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让奇怪的现象消失,让社会不奇怪起来。
来自:《学习时报》
版权所有:澳门传真正版承办:澳门传真正版
地址:开封市市民之家五楼 邮编:475000 邮箱:[email protected] 网站备案号:豫ICP备12001764号-1
技术支持:郑州信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